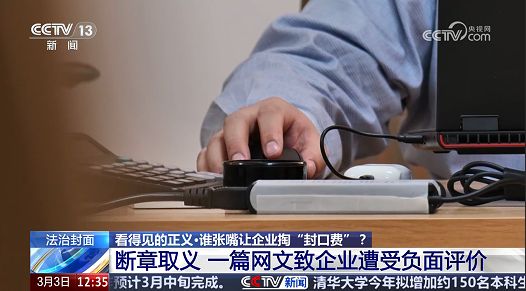文/张海青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文/张喜鸽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中国古代有“事可从经,亦可从权”的智慧。它告诉我们,在处理事务时既可以遵循既定的原则和规范,也可以根据现实需要采取灵活的应对策略,从中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平衡。结合我国的侦查制度,一般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负责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在必要的时候,检察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安机关管辖的部分案件立案侦查,能够督促公安机关提高办案效率,实现个案正义,这是法治国家背景下保障侦查权健康运行的优项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任何一项公权力都应当接受监督。当公安机关对部分案件不宜侦查或者怠于侦查时,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应及时“补位”,依法追究犯罪,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中,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令人关注,2023年全国查办176人,2024年查办263人,机动侦查职能从“沉睡”到有效激活,逐渐进入人民群众视野。
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包括直接侦查、机动侦查、补充侦查三部分。直接侦查是指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14个罪名犯罪,可以立案侦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对该14个罪名也有立案调查权,因此检察机关的直接侦查不具有专属性。补充侦查是在审查起诉环节,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一般由审查起诉部门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因这类侦查的启动条件是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具有灵活性、机动性,被形象地称为“机动侦查”。
机动侦查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它由检察机关专属行使,具有检察权的属性和特征。它源自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二是它具有侦查权的特征和权能。“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具有一定的秘密性和强制性。三是它有别于常态化的侦查权,实践中往往“备而不用”。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它只是在必要时行使,防止出现不依法、不及时立案等情形,启动条件受到严格的程序制约。四是具有保障性。机动侦查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起到内在的监督作用,督促公安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正确履行侦查职责。
机动侦查的行使有利于强化法律监督。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内容和对象不仅在于诉讼活动,还应包括行政执法活动等领域。直接侦查仅限于“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14个罪名案件。机动侦查拓展了法律监督的范围,从刑事诉讼活动走进国家机关管理活动;从对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扩大到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的侦查;从小范围的职务犯罪侦查,延伸到包括重大刑事犯罪的具有广泛意义上的职务犯罪侦查。所以,做好机动侦查工作,对于加强诉讼监督、补强执法监督短板,具有重要意义。
立案监督不是机动侦查的前置程序。立案监督是指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检察机关依法予以监督纠正的情况。对符合机动侦查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具有裁量权、选择权,既可以立案监督,又可以机动侦查,如果立案监督后公安机关仍不立案的,可以径行机动侦查。需要说明的是,2012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61条明确机动侦查前应当立案监督。该条规定:“对于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立案侦查。”这一定程度上导致机动侦查沦为“沉睡条款”。201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删除了该内容。
机动侦查与回避具有密切关联。回避制度源于英国自然正义法则,该法则的一项基本要求就是“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防止司法官因私情、私利,而在办案中出现偏私。西方不少国家甚至确立了“无因”回避的制度,只要当事人对该法官办理案件的公正性有合理怀疑的理由就能成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的回避有四种情形,范围相对较窄。从实践情况看,当前检察机关查办的机动侦查案件,多为公安民警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这些案件,个别公安机关采取调整岗位、政务处分处理,立案侦查的较少,移送监察、检察机关的更少;即使立案侦查,甚至异地交办,也难以摆脱“瓜田李下”嫌疑,办案公信力较弱。此时由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既有利于贯彻回避制度,又可以消除误解,可谓“急人之困”。如检察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由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如涉嫌普通犯罪则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减少“自己人查自己人”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诟病。
机动侦查“重大犯罪案件”的认定可以考虑三个维度。第一维度是重罪刑,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看是否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二是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罪名的量刑结构设置,如果该罪名的量刑有基本犯罪档、情节严重档和情节特别严重档,以后两档为重大犯罪;如仅有前两档的,以第二档为重大犯罪;如果只有基本犯罪档,则不构成重大犯罪。第二维度是重罪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规定的八种严重犯罪,认定属于“重大犯罪案件”没有争议。第三维度是社会影响。一些案件虽然法定刑较轻,但因引发群体性事件、网络重大舆情等而造成较大范围的恶劣影响,或者在全国及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也应属于“重大犯罪案件”。
机动侦查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对公安民警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公安机关不宜侦查,由检察机关机动侦查只是最初起点。当前检察侦查主责主业是直接侦查,如果机动侦查查办的是司法工作人员,应注重深挖是否有14个罪名犯罪,一并办理,做到机动侦查、直接侦查同频共振。另外,对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如存在久侦不结、怠于侦查等情形,检察机关既可以开展侦查活动监督,督促加快进度,也可以机动侦查,促进依法及时追究犯罪。
机动侦查案件应当体现比较优势。该案件原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在特殊状态下机动侦查,检察办案应当体现出优越性,才能保障行稳致远。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一是高起点定位。“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是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要通过机动侦查,把案件办成精品、典型案例,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二是立足一体化。机动侦查是最高检、省院事权,作出决定后,由设区市以上检察院立案侦查,一般由基层检察院审查起诉,故可以视为是举全省检察机关之力办案,“三个效果”应更为优质。三是务必做“减法”。办理机动侦查案件不能一哄而起,轻易“出手”,而应聚焦有影响、有示范引领意义的案件,办深办透。一般案件,可通过立案、侦查活动监督等方式督促公安机关办理。四是体现及时高效。检察机关办案需要体现高质量、快节奏,实现“看得见的正义”。五是自觉接受监督。省检察院要加强对下管理,办案单位根据需要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情况,审查起诉环节接受内部监督,再经“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检验,并及时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事可从经,亦可从权”,可视为法律规定的“有原则必有例外”。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难以实现司法公正、无法消除社会误解,特别是陷入“查自己人”困境时,可以舍经从权,启动检察机关机动侦查,依法追诉犯罪,适应现实需要,回应社会关切,把法律规定的公平正义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知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