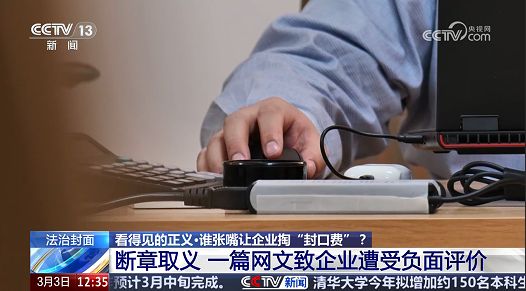文/刘松茂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
一、基本案情
李某是某连锁超市某分店的负责人,受超市全权委托,负责处理超市商品被盗后的相关事宜。李某在处理一起商品被盗案件时,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提出1万元的赔偿金要求,同时表示若张某不支付该笔赔偿费用,将不予出具谅解书,并会要求公安机关对张某从严惩罚。尽管侦查机关已经查明张某实际盗窃的商品价值仅为2100元,但在李某的威胁和压力下,张某为了拿到谅解书,最终支付了1万元给李某。李某收到这笔赔偿金后,将其中的2100元上交给了超市,将剩余的7900元占为己有。随后,李某代表超市向张某出具了谅解书,并请求侦查机关对张某从轻处理。
二、分歧意见
关于李某的行为定性,存在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李某作为受超市全权委托的负责人,在处理商品被盗案件时,利用自身职务所赋予的便利条件,如决定是否出具谅解书或向公安机关提出更为严厉的处罚建议等权力,对张某施加压力,要求其支付高额赔偿。然而这里的赔偿金,应当视为对超市因盗窃行为所遭受损失的补偿,其所有权应归属于超市。李某私自占有的行为侵犯了超市对该笔赔偿金的所有权,属于利用职务之便实行的侵占行为,因未达到职务侵占罪的入罪标准,因此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李某主观上带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即他并非单纯地为了维护超市的权益而要求赔偿,而是出于个人私利。在客观上,李某通过不出具谅解书等手段对张某进行威胁,利用张某对法律制裁的恐惧心理,强迫其支付远高于实际损失的赔偿金。在收取赔偿金后,李某将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据为己有,这一行为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李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即李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一)李某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内容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数额较大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李某的行为不满足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如下:一方面,李某的犯罪行为不满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构成要件。虽然李某作为超市分店的负责人,并利用其职务身份向犯罪嫌疑人张某索取高额赔偿金,并最终将这笔赔偿金占为己有,这种情形在表面上似乎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但实则不然。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所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据为己有的财物是基于行为人的职务(或业务)所占有的本单位财物,而不是指占为己有或者据为己有的行为本身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本案中,李某所据为己有的赔偿金并非直接源于其作为超市负责人的职务所直接占有的财物,而是李某利用了职务身份所带来的“优势”和影响力,对张某实施了威胁,从而获取了赔偿金。这种利用职务身份的行为,虽然对实施犯罪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但并非刑法意义上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李某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利用了其职务身份,但实质上并未满足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李某的犯罪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不是超市的财物,不满足“将本单位的财物占为己有”这一构成要件。职务侵占罪犯罪对象的“本单位财物”包括单位现存的财物和确定的收益。然而,李某所要求并占有的高额赔偿金远超过了超市因盗窃事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多出的部分并非超市的正常经营所得或已确定的收益,而是李某通过不正当手段从张某处索取的。因此,从犯罪对象的角度来看,李某的行为也不符合职务侵占罪中犯罪对象的要求。综上,某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二)李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明确要求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取得财物,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这里的胁迫,是指以恶害相通告,并非仅限于对生命、身体、自由或名誉的直接威胁,而是可以涵盖任何足以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的恶害。另外,李某所告知的恶害来源既可以是其自己(如不予出具谅解书),也可以是第三方(如公安机关可能施加的法律制裁)。这些恶害的实现本身也并不要求具有违法性。在本案中,李某不予出具谅解书的行为以及张某可能面临的法律制裁,虽然都是合法的行为或程序,但它们与张某是否会受到刑事处罚以及处罚的轻重密切相关。正是这两种看似合法的“恶害”,在李某的巧妙操作下,足以使张某因为担心刑罚的严厉性而产生强烈的恐惧心理。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张某被迫处分了自己的财物,以换取李某的谅解和可能的法律宽容。李某则因此取得了财物,导致张某遭受了实际的财产损失。
敲诈勒索罪的责任要素除故意外,还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本案中,超市授权李某全权处理超市被盗事宜,旨在维护超市的合法权益和日常运营秩序。然而,李某的行为显然超出了这一授权范围,李某并非在履行职务时维护超市利益,而是利用职务身份赋予的权力,对张某实施了恐吓行为,以达到非法索取财物的目的。另外,在敲诈勒索过程中,行为人通常会利用某种借口或滥用权利来恐吓被害人。李某正是通过威胁不予出具谅解书,以及暗示张某可能面临的法律制裁这两种合法的“恶害”来恐吓张某。这些威胁手段使得张某因担忧可能面临的严厉刑罚而产生恐惧心理,进而被迫支付了超额的赔偿金。
李某的行为不仅触犯了敲诈勒索罪的法律规定,还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应当以犯罪论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明确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在此案中,虽然超市的实际损失为2100元,但李某通过恐吓手段非法占有的金额高达7900元,这一金额显然符合敲诈勒索罪中“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且其犯罪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主客观要件,构成敲诈勒索罪。
将李某的犯罪行为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是对其行为性质的合理评价,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具有重要意义。敲诈勒索罪与职务侵占罪虽同属侵犯财产类犯罪,但二者在犯罪对象、性质及影响上存在区别。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对象直接针对被害人的个人财物,不仅导致被害人经济上的损失,还可能因暴力或胁迫手段给被害人带来心理创伤和不安。而职务侵占罪则主要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所产生的影响多限于单位内部的经济秩序,不直接对个人的财产权益造成损害。此外,将李某的行为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还能够震慑潜在的犯罪分子,防止更多具有特定职务身份的人利用这一影响力索取不属于单位的非法利益,减少类似犯罪的发生,更能够增强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和法治信心,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综上所述,李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对于李某的处理,可以根据其认罪态度、前科、赔偿等情况依法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