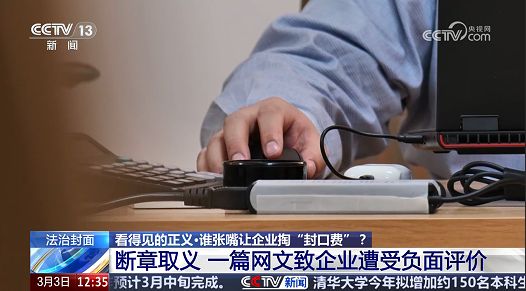文/盛振宇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检察院
文/王霞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检察院
一、基本案情
张某原系某物流园的保安,看到物流园的工作人员在联系货主或者承运人时,都是通过网络平台交流,并不到实地查看,便想利用双方的信息差来骗钱。2021年6月,货主黄某在某网络平台上发布货物托运信息。张某当日搜索到该信息后,谎称是车队负责人,约定以人民币20000元的价格帮黄某运送货物。次日,张某又谎称自己是货主,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信息,后以人民币22000元的价格委托承运人刘某运输该批货物。后刘某按照约定将货物从江苏运至山西某地,承运过程中实际支出工资、油耗、过桥路费共计13000余元。卸货后,黄某按约向张某支付运费人民币20000元。收到该款后,张某即将货主黄某和承运人刘某的微信、电话拉黑。
二、分歧意见
对张某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不构成诈骗罪。诈骗罪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者个人的财物,不能随意拓展或者延伸,而本案中张某实际骗取的是承运人刘某提供的运输服务,不属于诈骗罪的范畴,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此不能认定张某构成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构成诈骗罪。虽然刑法规定诈骗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但是财物既包括物,也包括财,即财产、财产性利益。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托运人支付相应运费的合同。张某假冒货主,通过欺骗手段使承运人刘某陷入错误认识,进而提供了运输服务,且该服务具有经济价值,属于财产性利益,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张某构成合同诈骗罪。张某与黄某、刘某签订的运输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涉及生产经营领域与市场秩序相关的合同。张某在签订、履行货物运输合同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非法占有承运人刘某的财产性利益,应当构成合同诈骗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张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应当以运输合同约定的运费认定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理由如下:
1. 诈骗犯罪的对象包含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双重属性。财产性权益是指狭义财物以外的无形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积极利益的增加(获得债权)和消极利益的减少(减少或免除债务)。侵财类犯罪对象一般限于公私财物,但是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诈骗罪的行为对象逐渐成为司法实践的共识。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收受对方当事人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担保债权就包含债权等财产性利益。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的,实际免除的是债务,亦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盗窃电信码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虽然盗窃的是电信码号、发票等,但是实际侵犯的是电信码号、增值税发票所体现的财产性利益,故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由此可以看出,财产性利益作为侵财类犯罪的对象不但符合群众认知,而且也契合现实需求。实践中,财产性利益也具有财产价值,多数可以转化为现金或者其他财物,是刑法应当保护的对象,如不将其作为犯罪对象考虑,不利于发挥其维护财产法益的作用。
2. 基于劳务所产生的财产性权益能成为诈骗犯罪的对象。财产性权益能否作为诈骗的对象,理论上曾有争议。张明楷教授认为:诈骗罪的对象应包含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可是,就劳务本身而言,因不具有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不能直接认定是财产性利益,但是基于劳务所产生的财产权能成为财产性利益。本案中,从表面上看,承运人提供的运输服务是劳务行为,一般不能作为诈骗犯罪的犯罪对象,但是承运人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已经产生了相关的劳动报酬,实际支出的油费、过桥路费、车辆损耗折旧以及相关管理费用。即使双方签订的运输合同无效或者说存在瑕疵,承运人基于承运事实上产生了债权,具有经济价值,具有转移可能性,应当是刑法应当保护的财产性权益,能够成为诈骗罪的对象。
3. 张某构成合同诈骗罪。首先,张某主观上有非法占有故意。主流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犯罪的非法占有既可以是在签订、履行合同之前,也可以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本案中,张某在搜索到货主托运信息后,假冒是车队负责人签订运输合同,又对刘某谎称自己是货主,欺骗刘某运输货物。其在整个过程中,既假冒了身份,又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且低进高出,收到真正货主支付的运费后立即将对方拉黑,非法占有的故意产生于签订运输合同前。其次,张某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假冒单位或他人名义,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自己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造。再次,尽管《刑事审判参考》第1048、1083号案例分别指出,“被告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交易时采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钱货两清的形式,合同的签订与否在本案中并不重要,故认定为诈骗罪”“不是只要与合同有一定关联,就必须认定行为性质属合同诈骗”;但是,《刑事审判参考》第308号案例强调,“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张某在签订、履行合同前,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均实施了欺骗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益,也严重破坏了运输市场秩序,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评价。
4. 本案合同诈骗的金额应当为承运合同约定的运费。本案有两个被骗人,但只有一个被害人,即实际遭受损失的承运人刘某,应当以被害人刘某的运费损失认定合同诈骗的犯罪金额。首先,该案货主黄某没有财产及财产性利益的损失,尽管他被骗签订了运输合同,但是他在支付运费的同时,货物如约运到了目的地,合同履行完毕,黄某实现了合同目的,其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没有提出撤销合同,甚至在此过程中,黄某支付的运费还略低于市场价,因此张某与黄某之间的运输合同成立并有效。同时,货主黄某与承运人刘某之间无合同之债,基于合同的相对性,承运人刘某不能直接向货主黄某主张权利,所以,黄某不属于是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其次,承运人刘某在本案中实际受到了损失,该损失包括其付出的劳务应当获得的劳动报酬,以及相关的油费、过桥路费等等,承运人既是运输合同中的被骗人,又是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第三,本案合同诈骗的犯罪金额应当为承运合同约定的运费22000元,而不仅仅是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实际产生的费用13000元。承运人刘某与诈骗实施人张某签订运输合同时,除了合同主体一方系冒名之外,双方关于运费的约定是平等主体之间意思自治的表示,没有隐瞒或者欺骗,也没有明显异于市场价,故由此产生的合同之债也即运输合同约定的运费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的金额,而不仅仅是承运人实际支出的那部分费用。退一步讲,假如承运人承运过程中产生了其他意外损失,也只能作为合同诈骗犯罪的相关后果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