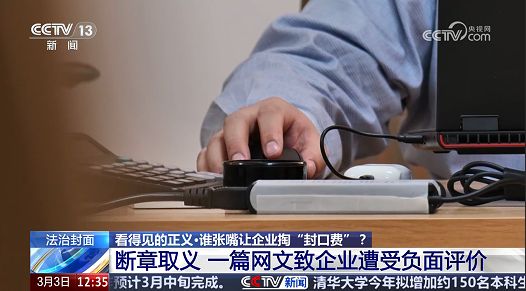文/魏冕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
文/李迪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
一、基本案情
史某与王某系同居男女朋友关系。2023年2月至4月期间,史某利用事先知晓王某的支付宝账户密码,在王某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通过操作王某手机转账的方式,窃取王某支付宝内钱款共计8万余元,后将窃得钱款用于赌博或偿还赌债,其间史某曾在赌博赢钱等情况下,多次向王某支付宝账户转回共计2万余元,直至被王某察觉后案发。
案发后,史某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并获得王某谅解。
二、分歧意见
该案在办理过程中,围绕盗窃次数及数额的认定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观点一:史某的行为属于多次盗窃,盗窃金额为8万余元。理由如下:史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近2个月的时间段内,在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转走王某支付宝内钱款,其行为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及“两高”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中“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应当认定为多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同时,史某将王某支付宝内资金8万余元转出后,相关资金已经脱离王某实际控制,属于犯罪既遂,因此本案犯罪金额为8万余元。史某转回2万余元在犯罪数额中不予扣减,其返还行为可以认定为退赃。
观点二:史某的行为属于多次盗窃,盗窃金额为6万余元。理由如下:史某向王某支付宝账户转回共计2万余元,在客观上没有减少王某支付宝账号内的资金,也没有给王某造成实际经济损失,对该部分资金不应认定史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故盗窃金额应该认定为6万余元。
观点三:史某的行为属于一次盗窃,盗窃金额为6万余元。理由如下:王某对史某的行为并不知情,王某的支付宝账户长期处于史某的实际控制下。史某基于同一个犯罪故意和犯罪目的,对同一个犯罪对象连续实施了盗窃行为,应该认定为一次盗窃。在王某未发觉的情况下,犯罪行为尚未结束,属于持续状态,因此应以犯罪完成时史某的实际损失认定盗窃金额。
三、评析意见
对于上述争议观点,承办人采纳第三种观点,即史某的行为属于一次盗窃,盗窃金额为6万余元,具体理由如下:
(一)取得电子账户控制权后的盗窃行为应集中评价为“一次”盗窃
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多次盗窃”是指“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目前尚未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何为“多次盗窃”进行明确规定。最高法《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对“多次抢劫”给予了认定标准,即“应以行为人实施的每一次抢劫行为均已构成犯罪为前提,综合考虑犯罪故意的产生、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客观分析认定”。“多次盗窃”是定罪情节,“多次抢劫”是量刑情节。实践中,对于“多次”盗窃标准能否参照前述《意见》规定进行认定,存在较大争议,但笔者认为举轻以明重,“多次抢劫”对“多次盗窃”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
第一,从犯罪主观故意来看。行为人基于独立的犯罪故意实施多个盗窃行为的,应当分别计算次数并认定为多次犯罪。而基于一个概括的犯意实施犯罪的,如在同一场所同时针对不同财物实施的,原则上应当计算为一次犯罪。本案中,史某基于一个犯罪故意和犯罪目的,即控制王某的账户、窃取占有账户内资金多次实施犯罪行为,应当认定为一个概括的犯意。
第二,从犯罪客体来看。如果行为人已经对所针对的概括或者同一财物形成了实际控制,例如,已经获取可以随时开启金库的钥匙,但因各种原因需要来回多趟搬运,后续的搬运行为只不过是行为人整体的一次盗窃行为有意化整为零的操作而已,当然不能认定具有多个犯罪客体。本案中,史某知晓王某的密码,已经形成了对王某支付宝中资金的实际控制,在此之后对账户内资金进行转出、转入时,应该认定为对同一个犯罪客体实施犯罪。
第三,从犯罪行为实施的客观因素来看。参照《意见》,对于行为人基于一个犯意实施犯罪的,如在一个地点同时对在场的多人实施抢劫的,若在同一地点连续地对途经此地的多人进行抢劫的;或在一次犯罪中对一栋居民楼房中的几户居民连续实施入户抢劫的,一般应认定为一次犯罪。本案中,史某出于同一犯罪目的,用较长的时间完成只需较短时间即可完成的犯罪行为,并且史某行为所引发的是构成要件结果量的增加,并非质的不同,属于刑法理论上的徐行犯,是罪数理论上单纯的一罪,应当按照一罪进行处断。
第四,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来看。根据最高检应勇检察长提出的“三个善于”,要善于在法理情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因此必须坚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及其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本案犯罪次数的认定直接影响到刑罚执行方式的确定,根据2023年江苏省高院、江苏省检《〈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中关于盗窃犯罪量刑的相关规定,“具有多次盗窃情形,且犯罪数额达到较大以上的”,一般不适用缓刑。本案中史某具有自首情节,已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并获得王某谅解,且二人当时系同居情侣关系,若坚持认定史某的行为属于多次盗窃,则难以对其适用缓刑。因此,将盗窃犯罪次数认定为“一次”,也更加有利于兼顾天理国法人情,实现个案公正与类案公正、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二)取得电子账户控制权后的盗窃数额应以实际损失为准
第一,从犯罪行为是否终结考量。刑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均认可“失控加控制说”作为盗窃罪既遂标准,即盗窃行为已经使被害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或者行为人已经控制了所盗财物。根据徐行犯理论,王某一直处于一次盗窃犯罪的行为过程中,既然犯罪行为尚未结束,自然应当以犯罪完成时史某实际转移走的金额,即王某的实际损失金额来认定具体盗窃犯罪数额。举一极端例子,甲进入乙屋内欲盗窃一昂贵劳力士金表,内心产生强烈波动,拿起金表后走至屋门口后又返回放下,反复数十次后最终拿表离开,犯罪金额无疑仅应认定为一只金表的实际价值,否则也与民众的朴素认知与常情常理相悖。
第二,从法益侵害性角度考量。盗窃罪的本质是一种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其结果是行为人的行为致使被害人丧失了对财物的占有,也就是通常所理解的盗窃罪犯罪数额为被害人财物的实际损失。特别是对于行为人取得对财物所在空间的控制后,对其控制空间之内的财物进行“窃取—归还”操作时,不应机械地以转移占有就构成犯罪既遂为标准来计算犯罪数额,而应以实际损失为标准来确定犯罪数额。本案中,史某最终给王某造成的实际损失为6万余元,即实质上侵犯了王某6万余元的财产法益。如果让史某承担侵犯8万余元的责任,则不符合法益保护的要求。
第三,参照“盗窃信用卡”数额考量。本案中,王某部分被盗资金来源于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史某在控制王某支付宝账户后,冒用被害人王某名义从支付宝绑定银行卡划拨资金进行消费的行为,虽然与传统“冒用信用卡”的行为不同,但基于支付宝与银行卡的关联绑定,使得支付宝和银行卡均以为系原卡主进行使用,进而自愿实施支付行为,符合“盗窃信用卡”的行为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即盗窃罪)定罪处罚,同时参考最高法《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对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其盗窃数额应当根据行为人盗窃信用卡后使用的数额认定。因此,该案犯罪金额也应为王某实际损失的6万余元。
四、案件处理结果
史某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巨大,构成盗窃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建议对其适用缓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罪名、认定的犯罪情节和量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