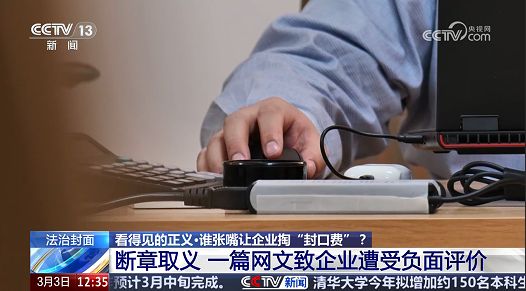文/刘亚茹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
文/陈鹏飞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
一、基本案情
郑某在担任某国有企业工程部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陈某在工程承揽方面提供帮助。事后,陈某为表感谢,向郑某表示愿意给予好处费。郑某直接要求陈某将13万元贿赂款转入某房地产公司账户,用于支付其名下一套房产的尾款。后陈某依郑某指示将13万元贿赂款转入房地产公司账户。
二、分歧意见
观点一主张,郑某的行为构成自洗钱犯罪。根据2024年8月施行的《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通过投资、买卖等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可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从主观方面分析,郑某明知该13万元款项为贿赂款,却主动要求陈某用于支付房产尾款,这表明其积极处置受贿赃款,主观上存在通过将赃款转化为房产来逃避法律对受贿赃款追查的故意,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故意。从客观方面分析,郑某主动要求陈某用贿赂款支付房屋尾款,这一行为实质上是将受贿所得转化为不动产形式,改变了违法所得的原始形态,符合洗钱犯罪中通过资产形态转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性质的特征。
观点二认为,郑某的行为不构成自洗钱。郑某用受贿赃款购买房产,本质上是受贿犯罪行为的延续,是受贿过程中收受财物的一种方式。当贿赂款转入房地产公司账户时,受贿犯罪既遂,根据一事不再罚原则,无需对该行为重复评价。从犯罪构成要件分析,郑某的行为仅符合受贿罪构成要件,即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郑某未实施超出受贿行为本身的、具有独立意义的洗钱行为,如借助复杂的金融交易,通过在不同金融机构间进行资金的频繁转账、虚假理财等操作,或者开展虚假贸易,虚构货物买卖、服务提供等交易场景来对赃款进行合法化处理。而且房屋登记在郑某个人名下,这种公开透明的物权归属使得资金来源和性质难以被有效掩饰与隐瞒,侦查机关对资金的追踪并未因此被切断。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郑某的行为不构成自洗钱犯罪。
我国洗钱罪立法有着清晰的演进脉络,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自1997年确立以来,历经三次修正,反映出立法者对洗钱犯罪认知的深化与打击策略的转型。1997年至2001年,洗钱罪以遏制特定犯罪为导向,将上游犯罪限定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四类,重点打击通过金融机构实施的洗钱行为,这一时期,立法主要聚焦于对特定严重犯罪所衍生的洗钱行为进行规制,旨在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防止犯罪分子利用金融体系清洗非法所得,确保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营不被犯罪活动所干扰。2001年至2020年,立法逐步扩大上游犯罪范围,将贪污贿赂犯罪等七类犯罪纳入,但延续“他洗钱”规制模式,将贪污贿赂犯罪等纳入其中,体现了立法对腐败犯罪等领域资金清洗行为的重视,进一步完善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体系,强化了对各类犯罪所得清洗行为的打击力度。直至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实现制度突破,将“自洗钱”单独入罪。此次立法考量具有双重维度:一方面,扩大打击范围以应对跨国洗钱、虚拟货币等新型犯罪挑战;另一方面,基于“法益保护升级”理论,将严重妨害司法追查、扰乱金融秩序的自洗钱行为独立评价。自洗钱行为不仅对司法机关追查犯罪所得造成阻碍,增加了司法成本,也对金融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将其独立评价能够更好地保护金融秩序和司法秩序这两大重要法益。
回归本案,郑某行为的法律性质需置于此立法演进框架下考察。其购房行为未采用跨境转移、虚假交易等专业洗钱手段,与立法意图打击的“破坏金融秩序和司法秩序”行为存在本质差异。具体理由如下:
(一)行为特征缺乏自洗钱独立性
若认定自洗钱犯罪,需要实施两个独立的犯罪行为。认定上游犯罪和自洗钱犯罪,需要各自符合独立的犯罪构成。上游犯罪行为人完成上游犯罪并取得或控制犯罪所得后,进一步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才属于自洗钱行为。郑某指示行贿人支付房产尾款的行为,虽然改变了资金存在形式,但本质上只是受贿行为完成的一种方式。郑某的行为没有超出受贿行为范畴,没有构建起独立的、符合自洗钱行为特征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行为体系。其购房行为没有创造新的资金流转路径来刻意掩饰受贿款来源,仅仅是受贿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属于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接收资金的行为,是上游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不宜重复认定为洗钱行为。
(二)主观上没有洗白赃款的故意
郑某的主观故意主要围绕受贿行为,也就是利用职务之便获取非法利益。其指示行贿人支付房产尾款,目的是完成受贿财物的收受,实现对房产权益的占有,并非通过房产购置刻意切断受贿款与受贿犯罪的关联,不具备洗钱罪所要求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的主观故意。假定郑某用他人银行卡收受贿赂款,并指示他人买房且房产登记在他人名下,此时主观故意才与自洗钱目的相符,但在本案中郑某并未实施此类行为。郑某利用受贿所得用于购买房屋,更多是为了获得该房屋的使用价值,并非为了洗白赃款。并且房产登记在受贿人自己名下,客观上未产生逃避监管的效果,亦无法切断犯罪所得和上游犯罪的联系,不具有洗白目的。从主观方面分析,郑某在实施该行为时,其内心的主导动机是获取房产这一实际利益,而非对受贿款进行合法化处理,这与自洗钱犯罪中犯罪分子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掩盖资金非法来源的主观心态截然不同。
(三)行为未实质干扰金融秩序和司法侦查
洗钱罪设立的目的在于维护金融秩序、保障司法活动顺利进行,进而实现追赃挽损。从郑某的行为表现来看,其并未对上述法益造成实质性损害。具体而言,一在金融秩序方面,郑某用受贿款购房,属于常规房产交易行为,与反洗钱法第2条规定的可疑交易特征不同。郑某购房时未利用金融机构进行资金拆分、混同或跨境转移,未引发金融机构对资金异常流动的警觉,未通过复杂金融手段破坏金融监管秩序。二是在刑事追诉环节,郑某的行为没有阻断涉案财物与本人的关联性,没有给司法机关的追诉带来额外成本。本案资金流向清晰可溯,司法机关可通过调取购房合同、银行交易流水等书证直接建立受贿行为与犯罪所得的关联。同时,涉案房产物权归属明确,司法机关可直接查封、拍卖,未额外增加司法成本。虽然房产交易增加了一定调查难度,但未超出受贿犯罪侦查的常规范畴。司法机关通过对受贿行为的调查,能够较为清晰地查明资金来源与受贿犯罪的关联性,不存在因郑某行为导致司法侦查陷入困境的情况,与自洗钱行为对司法侦查造成严重阻碍的特征不符。三是在追赃挽损方面,司法机关能够直接将该房产认定为受贿所得并依法处置,实现对犯罪所得的挽回,郑某的行为未对追赃挽损工作造成实质性干扰。
综上所述,准确界定自洗钱犯罪,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严格把握行为独立性与法益侵害性双重标准。在郑某案中,受贿行为与财产处分具有时空连续性和目的同一性,未产生新的法益侵害,不符合洗钱罪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应避免机械适用法律,防止不当扩大洗钱罪适用范围,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