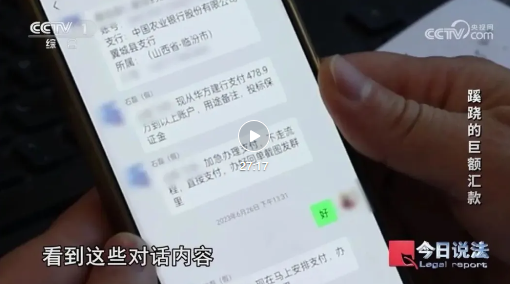——兼谈组织卖淫罪中“三人以上”标准的实践把握
文/刘志华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检察院
一、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起,马某和妻子付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所承包的浴室组织失足妇女A、B进行卖淫活动,马某负责管理收入、约定分成、对抗检查、通风报信等活动,付某进行协助。2020年12月底,失足妇女C加入卖淫人员队伍,卖淫人员达到三人。2022年1月,失足妇女A离开浴室,马某组织卖淫人员恢复为2人。2023年9月,失足妇女D加入卖淫人员队伍,马某再度组织三人进行卖淫活动,直至2024年该浴室关闭。据统计,马某、付某组织三人卖淫期间获利84.5万元,组织二人卖淫期间获利16.8万元。
二、评析意见
关于本案马某和付某的行为如何处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数罪并罚,马某和付某的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和容留卖淫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控制卖淫人员达到三人以上的,应当认定为“组织他人卖淫”。组织卖淫人员三人以上应当是指在指控的犯罪期间,管理、控制卖淫人员不仅达到三人以上,而且三人以上的卖淫人员在被管理、控制的某个时间段必须存在交叉、重叠,即同时达到三人以上。组织卖淫罪的构成应当以具有“组织性”为前提,组织性不只是体现在行为人的组织、管理行为,还体现在将单个卖淫人员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整合为三人以上的稳定的卖淫团体。组织卖淫罪是重罪,在同一时段的卖淫人员达到三人以上才能体现出一定的组织性、规模性,进而体现出该行为的危害性。从“解释”的体系结构上看,“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不可以累计计算,“解释”规定卖淫人员人数的共有7处,其余6处明确“卖淫人员累计达xx以上的”,因此对组织卖淫罪的入罪标准“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不能做扩大解释,进行累计计算。根据“解释”规定,容留二人以上卖淫构成容留卖淫罪。综上,对于马某和付某组织三人卖淫期间的行为认定为组织卖淫罪,对马某和付某组织二人卖淫期间的行为认定为容留卖淫罪。鉴于两部分行为不属于同一时段,采取数罪并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以单一罪名认定,马某和付某的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犯罪所得为84.5万元。马某、付某自2020年6月起即开始实施组织卖淫活动,组织、管理行为前后一致,只是卖淫人员存在客观变化情况,根据不同时段以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进行数罪并罚,属于对同一行为而进行数罪并罚,这明显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根据“解释”第三条,在组织卖淫犯罪活动中,对被组织卖淫人员有容留卖淫行为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择组织卖淫罪处罚,也即容留卖淫行为被组织卖淫行为所吸收,不适用数罪并罚。在马某和付某组织二人卖淫的时段内,必然容留了该二人卖淫,该容留行为也属于组织卖淫犯罪活动中实施的容留行为,仅需要依照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无需单独定罪,但该部分非法获利不应计入组织卖淫犯罪金额,基于任何人都不应从违法犯罪中非法获利的原则,将该部分非法获利16.8万元没收、上缴国库即可。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以整体行为认定,马某和付某的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犯罪所得为101.3万元。马某和付某的组织卖淫行为具有连续性、同类型的特征,不宜简单根据不同时段的人数进行切割,而应根据其总体行为认定构成组织卖淫罪,且非法获利100万元以上,属于组织卖淫罪中的“情节严重”。
三、笔者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从行为的完整性看,组织卖淫行为已经构成组织卖淫罪的,不能将“未满三人”组织卖淫行为予以扣除。根据“解释”规定,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控制卖淫人员达到三人以上的,应当认定为“组织他人卖淫”罪。组织卖淫者人数多少、规模大小不影响组织卖淫行为的认定。从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来看,组织卖淫人员三人以上为入罪标准,其他未满三人的组织卖淫行为不单独构罪,但并不阻却刑事违法,仍应属于组织卖淫行为。司法实践中,不少地方将组织卖淫罪的准入客观要件理解为“组织卖淫人数同时达到三人”,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对于确实出于主观故意,客观上在部分阶段也达到了犯罪标准的组织卖淫行为,机械地将其他阶段的组织卖淫行为从犯罪事实中扣除是否合理。笔者以为,对于已经构成组织卖淫罪的犯罪行为,从属部分的组织卖淫行为也应作为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违法所得应当进行累计。从主观方面来说,行为人实施组织卖淫行为的主观方面是一脉相承、稳定和连续的,卖淫人员的变化并非行为人主观不愿组织三人以上,而是因为受客观条件所限不能。从客观方面来说,同类违法事实已经构成犯罪时,其他违法事实当然应该累加。譬如盗窃、诈骗、抢夺已经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当然不会因为已经达到犯罪标准而将其他单独不构成犯罪的笔数不予累加。因此,在本案中马某和付某已经构成组织卖淫罪的前提下,其不足三人的组织卖淫行为和非法所得也应纳入量刑情节。
其次,从行为的认定标准看,组织卖淫行为的认定不宜简单根据人数决定,而应该更加关注“组织”内涵和行为延续。根据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界定行为人究竟是组织卖淫罪还是容留卖淫罪时,关键还是在于如何看待其行为的“组织”特征。本案中,马某和付某并非只是简单地对卖淫女进行容留,还实施了管理收入、约定分成、对抗检查、通风报信等一系列活动,完全符合组织卖淫的行为特征。简单地因为人数不够,将组织卖淫行为降格认定为容留卖淫行为,尤其是在同类组织卖淫行为具有连续性的情况下,将同一段组织卖淫行为分别界定为容留卖淫罪和组织卖淫罪,既不符合法律事实认定的基本逻辑,也不符合社会公众的常规认知,只能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情理与法理相偏离的悖论。因此,本案中马某和付某的行为不宜分段认定为容留卖淫罪和组织卖淫罪。
最后,从司法实践看,以“唯人数论”对组织卖淫犯罪进行查处容易造成执法漏洞。在司法实践中,组织卖淫者与卖淫人员的联系往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在一些非特定场合卖淫的案件中,两者之间的联系更加具有封闭性、非共享性等特征。一味强调“组织卖淫人员同时达到三人”,很容易被不法分子从证据方面钻法律空子,如避免同时组织多人卖淫,卖淫人员相互直接进行信息隔离等。就组织卖淫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而言,人数也并非衡量该类案件社会危害性的唯一标准,过于凸显单一标准,忽视该行为的综合危害性,虽然保持了刑法适用的谦抑,但却可能造成新的法律适用“盲点”。综上所述,不仅对于连贯性的组织卖淫案件不宜进行行为切割,即便对于常规的组织卖淫罪认定,也有必要重新审视其犯罪准入门槛,将人数标准更好融入社会危害性综合评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