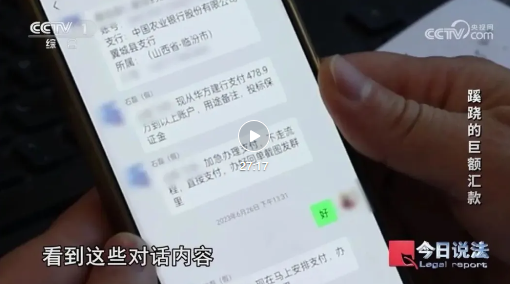文/黄晋涛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检察院
文/王鑫
上海市嘉定区华亭消防救援站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20日16时许,徐某驾驶电动三轮车,在机动车道内由东向西行驶至路口处右转弯时,与同向后侧非机动车道内直行的丁某南驾驶的电动二轮车相撞,丁某南受伤后被送医抢救。7月21日,丁某南因脑外伤术后迁延性昏迷等转院治疗。术后,主治医生建议转第三方医疗机构看护。经评估,丁某南病况严重,不具备收疗条件,11月13日予以出院。2021年1月14日,经鉴定,丁某南符合“植物生存状态”,其损伤构成重伤一级。同年11月13日,丁某南死于家中。同日,经再次鉴定,丁某南符合颅脑损伤继发感染死亡特征。
分歧意见
基于罪责自负的基本原则,一个人只能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故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必须明确。本案争议在于,丁某南出院一年后死于家中,其死亡结果与徐某交通肇事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存疑,对徐某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产生两种意见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丁某南出院后病状稳定,其在事后近一年半时间死亡,无法排除异常因素介入致死,徐某仅需承担交通肇事导致丁某南重伤一级的民事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丁某南出院后病状稳定但病况严重,虽然死亡结果距事发时间较长,仍无法阻却二者的因果关系,徐某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合乎逻辑、规律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丁某南虽在事发后被及时送医治疗且经历较长时间病情稳定期,但根据证人证言、伤情及死因鉴定书和相关病历记载证实,丁某南的死亡结果和徐某的交通肇事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理由如下:
第一,具有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现实前提。交通肇事罪的危害行为即行为人存在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危害结果即“人重伤、死亡”或“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本案中,徐某驾驶电动三轮车行驶至路口右转弯进出道路时,妨碍非机动车道内丁某南驾驶的电动二轮车的正常通行,其行为违反了《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车辆进出道路,应当让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制定机关为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其为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属于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一种,故徐某具有危害行为。事故发生后丁某南受伤被送医抢救治疗,终因颅脑损伤继发感染而死亡,符合“人死亡”的危害结果。故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具有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客观现实前提。
第二,不具有结果回避可能性但具有注意义务履行可能性。结果回避可能性,即行为人实施了注意义务的行为,其行为与结果也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是当行为人实施合义务的行为也不能避免结果的发生时,不能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通过查看交通监控视频发现,案发当日天气晴朗,事发路口附近无遮挡物,视线良好,客观上不存在影响观察的环境因素。又通过查看两车相撞前画面发现,徐某右转弯前并未通过反光镜或侧头观察后方是否来车,或打开转向灯向后车警示车辆动向,其没有实施注意义务的行为。假使徐某实施了观察后方车况的行为,那么本案事故完全有可能避免,故其不具有结果回避可能性。过失犯注意义务的核心是危险回避义务而非结果回避义务。本案中,徐某作为接受过义务教育的成年人,驾驶车辆上道路行驶应当预见到如果不遵守道路交通规则可能会发生包括人死伤或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的后果。避免这种风险产生的有效路径就是履行注意义务,即遵守交通规则,这也符合当下一般公众的社会认知、行为基准及刑法评价的一般公众的接受程度。案发当日无不利于履行安全注意义务的环境因素,徐某本人亦无影响履行义务的身体因素,客观上其车辆与丁某南存在观察后可保持安全的距离及车速,具备注意义务履行可能性。
第三,不存在异常介入因素。“介入因素”是指“介入在初始不法行为或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独立的原因。它改变了事件的自然顺序,产生了并非紧接着发生的、无法合理预见的结果,它可使损害的结果改变。”徐某提出无法排除异常因素介入致死的理由是丁某南术后未在医疗机构继续接受治疗而居家由近亲属照护,存在照护不到位的可能。在因果关系发展进程中,如果介入了第三者的行为、被害人的行为或特殊自然事实等其他因素,则应当考察介入因素的异常性大小、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力大小、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等情形,进而判断前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介入因素的异常性大小。介入因素本身的异常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因果关系的成立与否,如果介入因素的出现并不是异常的或者异常性较小,则先前行为是危害结果的原因,反之则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便被介入的异常因素所切断。而判断是否属于异常因素,则必须审查先前行为与介入因素的因果关系:(1)是不是由先前行为所必然引起,(2)是不是常常伴随先前行为所发生,(3)是否存在几乎不发生的情况,(4)是不是和先前行为完全无关地发生。无论是直接因果关系,还是间接因果关系的认定都应受到近因原则的限制,不能舍近因,求远因;更不能近因无责,归罪远因。徐某的肇事行为在本案中即属于近因,送医抢救、转院治疗、居家照护等作为交通事故引起的客观介入因素,具有必然性、不可抗力性,普遍存在于交通事故中,且无法独立于交通事故存在、发生,亦不存在事发后不对伤者进行救治的可能,故丁某南近亲属的居家照护行为并非异常因素。二是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力大小。通过询问主治医生、相关病症专家、法医明确照护本案被害人所需关键条件,又经实地查看被害人居家场所、询问被害人近亲属及照护人员查明丁某南居家期间在休养环境、饮食补给、精神安慰、医疗器械等方面均获得了良好支持,超出医嘱标准及预期状态,丁某南近亲属的照护行为对死亡结果并未产生积极作用,更不会阻断徐某肇事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对死亡结果发生不存在作用力。三是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在认定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客观关联时,还应当从危害行为对危害结果发生所起作用的大小上分析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内在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不能机械地要求二者之间必须存在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同时,也不能脱离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合乎规律的联系,无限制地放宽。通常而言,如果危害行为必然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则前者对后者的发生起到直接的、必然的作用。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不会发生,则前者对后者的发生所起作用大。本案中,徐某的肇事行为直接导致丁某南呈植物人状态,其又因颅脑损伤长期卧床引起继发感染而死亡。交通事故并不必然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徐某的危害行为也无法确证对丁某南颅脑损伤继发感染死亡的结果起到直接必然的作用,但如果没有徐某的危害行为则丁某南的死亡结果就不会发生,该危害行为作用力大。综上,本案不存在阻确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异常介入因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徐某的交通肇事行为致丁某南严重受伤,其近亲属的照护是必然行为之一,不属于异常介入因素,徐某的危害行为与丁某南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故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
判决结果
2023年8月24日,Y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徐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Y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0月10日,Y市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10月20日,原审被告人徐某向W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12月19日,W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判决已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