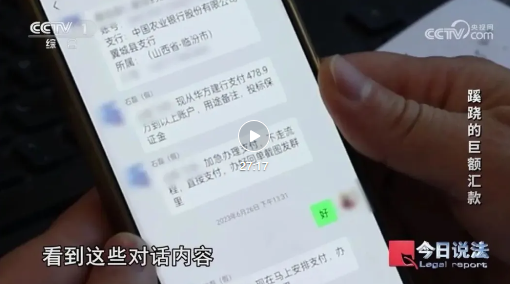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案例
甲系某监狱民警,负责管教罪犯乙、丙、丁等人。甲在履职期间,受乙、丙、丁之托,擅自与3人近亲属联系,收受其近亲属给予的香烟、购物卡、茶叶等财物,帮助对外传递信息、夹带食品进监等,后甲以“带五留五”(罪犯近亲属给其1000元,其购买、夹带物品价值500元,自留500元)形式获利。经统计,甲共接受乙、丙、丁近亲属财物约5万元,夹带进监物品价值约2万余元。一年后,在讨论对罪犯提请减刑的该监区全体民警会议上,甲明知乙、丙、丁违规对外传递信息、贿赂监管民警等行为违反监规,不符合减刑条件,而予以包庇、隐瞒,未提异议,书面签字同意呈报减刑,致使3名罪犯分别被减刑6个月至9个月。
甲违规“捎买带”获利,在提请减刑中不提异议,致使不符合减刑条件的罪犯被减刑,应当如何评价?
评析
刑罚执行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公里”,罪犯在监狱服刑改造是刑罚执行的主要方式之一。监狱民警违规“捎买带”是一种权钱交易行为,它严重破坏监管秩序,引发罪犯效仿,增加监狱管理难度,使得罪犯难以在监狱中接受有效的教育和改造,从而影响其重返社会后的表现。依法查办监狱民警“捎买带”渎职犯罪,维护“大墙”内的司法公正,始终是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重点。
上述案例,第一种意见认为,甲超越职权违规“捎买带”行为,导致服刑罪犯处遇不平等,个别罪犯在监狱享有“特权”,监管秩序被严重破坏,涉嫌滥用职权罪;甲明知相关罪犯不具有减刑条件,而包庇隐瞒,涉嫌徇私舞弊减刑罪,应当数罪并罚。第二种意见认为,甲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减刑罪,是违纪行为,不是犯罪。第三种意见认为,甲涉嫌徇私舞弊减刑罪。
我们认同第三种意见,甲涉嫌徇私舞弊减刑罪。1979年刑法规定了徇私舞弊罪,1997年增设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目的是惩治侵害刑罚变更执行公正性的行为。
减刑制度是我国刑罚执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缩短刑期,激励罪犯积极改造,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根据刑法规定,减刑分为特殊减刑和普通减刑。特殊减刑是指,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罪犯,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普通减刑是对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减刑体系中普通减刑居多。普通减刑又分为法定减刑和酌定减刑。法定减刑是罪犯因有重大立功表现应当减刑。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一般立功表现,可以减刑,此为酌定减刑。
监狱民警和罪犯是法律框架下的特殊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包含强制性、教育性,也涉及人权保障和改造目的。监狱民警依法行使监管权力,检察机关依法进行刑罚执行监督,保护罪犯的合法权利。一般情况下,监狱民警、罪犯不应有监管之外的过多交集。
监狱民警“捎买带”之“捎”,通常是指顺便带东西,“买”是购买,“带”是携带进监。“捎”“买”并列或者单独存在,落脚于夹带进监。通常表现为罪犯家属通过向监管民警行贿、预缴“生活费”等方式,由民警代为采购商品(如香烟、食品、日用品等),民警成为“代购”。如果捎带违禁品,引发犯罪的,可能涉嫌滥用职权罪。
我们认为,甲在乙、丙、丁的减刑过程中徇私利,存在包庇等舞弊行为,应当整体评价,以徇私舞弊减刑罪定罪处罚。首先,罪犯乙、丙、丁因甲的不法行为,不应减刑却实际获得减刑。
本案中,乙、丙、丁三人授意近亲属向甲变相行贿,利用甲作为管教民警的职权便利,撇开检查环节,夹带物品进监。从罪犯及其近亲属、监狱民警的行为看,是一种行、受贿的对合行为,侵害了监狱民警职务廉洁性,使相关罪犯在监管场所得到特殊照顾,监狱法规、监管秩序被严重破坏,可以得出三名罪犯未认真遵守监规,没有悔改表现,不符合减刑的前提条件。
其次,甲明知监狱管理规定及自身管理职责,有徇私舞弊行为。监狱法规定,监狱的管理人员是人民警察;监狱的人民警察不得索要、收受、侵占罪犯及其亲属的财物及违反规定,私自为罪犯传递信息或者物品。作为监狱规定和纪律,监狱民警甲应当明知。根据司法部《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提请减刑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结合罪犯服刑表现,由监区人民警察集体研究,并提出减刑建议,再依次通过监狱、法院等予以裁定减刑。可见,监区是提请减刑的首要环节,监区、管教民警是“第一道”防线。甲无视法律规定和职责要求,违反规定,擅自为服刑罪犯夹带物品获取经济利益,徇私动机已通过客观行为实现。
再次,解释法律应当先从法律文本的基本、普通含义出发,使法律具有可预测性。徇私舞弊减刑罪,包括徇私、舞弊、减刑三个要素。从文义看,徇私是一种主观动机,为了私情、私利而做不合法的或错误的事。舞弊通常包括捏造事实或者伪造材料,用不正当或者欺骗的方式。明知罪犯不符合减刑条件而予以隐瞒,就是舞弊行为。因徇私和舞弊相辅相成的密切关联性,司法实践中作为同位语对待。本案中,甲违反监狱管理制度,违规夹带物品进监,民警与罪犯各取所需,此为徇私利;甲作为监管民警,明知罪犯不符合减刑条件,而背弃职责要求,在监区提请减刑会议上予以隐瞒、包庇,报请减刑,当然是舞弊行为;上述行为导致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被减刑,徇私、舞弊与罪犯被减刑具有连贯性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三要素已经齐备。需要说明的是,徇私舞弊减刑罪是行为犯,只要存在违法报请减刑的行为,就构成犯罪。如果罪犯实际减刑,量刑上对监狱民警则从重考虑。
甲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违规“捎买带”的本质是滥用职权和受贿,但甲与相关罪犯权钱交易的指向性并不清晰,缺乏直接的请托行为,且未达到受贿罪的立案追诉标准。甲也不构成滥用职权罪。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罪需要犯罪后果。2012年《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包括:造成人员伤亡(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等);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在非物质性的危害结果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引用较多,也争议较大。但实践中,司法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引发犯罪分子再犯罪,评价为恶劣社会影响,入罪没有争议。本案缺少危害后果。
综上,甲的行为分别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应当整体认定为徇私舞弊减刑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