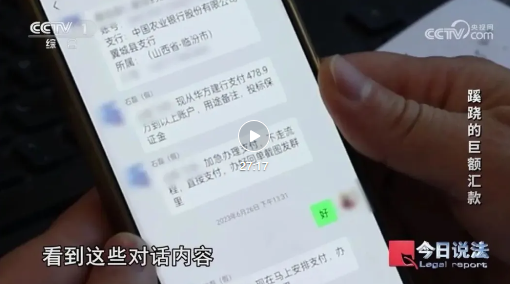江苏省镇江市人民检察院王敏
【基本案情】
某县自然资源规划部门(以下简称规划部门)向该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执法局)发送了《违法建设查处告知函》,主要内容为群众举报李某的公司厂房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用途进行建设,请该县执法局依法查处。在查处过程中,该县执法局向本县规划部门发出《违法建设认定函》,县规划部门回函,“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县执法局遂依据该回函及其他相关证据对李某作出了《限期拆除决定书》。李某不服,向法院起诉该执法局,请求法院撤销执法局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执法局答辩,其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依据的是规划部门的回函,并在庭前、当庭运用该份材料进行答辩。李某败诉,遂向法院起诉规划部门,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规划部门所作的违法建设认定函。
【意见分歧】
在司法实践中,对规划部门作出的违法建设认定函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存在争议的,各地实践操作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规划部门应城市管理部门要求就违法建筑所作规划认定意见的回函,系不同行政机关之间内部协调的文件,属于行政机关之间依照各自职权进行咨询、答复的内部行政行为,其不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对外也不产生法律效力,不具有独立可诉性。
第二种意见认为,规划部门应城市管理部门要求就违法建筑所作规划认定意见的回函,实质上是对涉案建筑物的性质进行了认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具有独立的可诉性。
第三种意见认为,要结合认定函内容的具体情况,看是否直接、现实地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综合认定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案件受案范围。
【意见评析】
我们同意第三种意见,认为要结合认定函内容的具体情况,看是否直接、现实地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案件受案范围。
(一)违法建设认定函的形式是否已经外化
内部行政行为只有外化,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才具有独立的可诉性。违法建设认定函是否可诉,主要看外化形式。外化的形式有以下两种,一种是规划部门通知或告知了当事人违法建设认定内容,或者将认定函送达一份给当事人。因为具有行政确认的特征,认定函的具体内容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了影响,所以具有独立的可诉性;一种是执法部门以违法建设认定函作为事实根据,向当事人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或者责令改正和罚款决定。虽然违建认定并未直接创设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它对行政相对人此后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因为规划部门认定的结论已经决定了城管执法部门的处罚种类。从此角度出发,违建认定行为完全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的有权起诉的规定。本案中,违法建设认定回复函属于第二种外化形式,且,执法局在庭前向法院提交了规划部门的回函,又在庭审中依据该份材料作为答辩,该回函的形式实质上已经外化。
(二)违法建设认定函是否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
所谓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是指行政行为为当事人设定了新的义务,直接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让当事人承担新的负担。规划部门作出的违法建设认定,虽然从形式上看是应执法局询问作出的内部复函,不是直接针对李某作出的,不具备外部法律效力,但其约束力已不仅限于被答复人,而是对李某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其一,根据我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规划部门有认定违建的职责,在其管辖范围内具有规划管理工作的行政职权。正因为其拥有该项职权,其才会积极向执法局作出回函。其二,该认定函对李某的建设行为进行了定性,规划部门在知晓涉案建筑取得规划许可的情况下,明确认定李某的建设行为“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这直接对李某建筑物的性质进行了确认。此时,认定函实质上给当事人设定了义务,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其三,该认定直接导致执法局将李某建筑物作为违章建筑予以处理,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直接产生了实际影响。执法局后续的处罚行为须以规划部门认定函为依据,并不具有对其进行审查甚至撤销的权力,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行为实质上只是规划部门违建认定行为的程序上的延续,没有执法局主体独立意志的体现。体现在本案中,执法局始终强调其《限期拆除决定书》也是根据规划部门认定函来作出的,只是按照程序执法。
(三)排除对违法建设认定函的可诉性将造成司法审查的空白
如果规划部门作出的违法建设认定函不可诉,则李某仅可就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提起诉讼。但执法局答辩其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依据的是规划部门作出的违法建设认定函。因司法审查的对象是执法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规划部门不是案件当事人,执法局亦无须提交证明该认定合法的证据,在行政处罚诉讼案件中,法院实际上无法对规划部门出具的认定意见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且,由于该认定属于公法上的职权行为,法院通常只能认可其效力。如此,相当于从根本上剥夺了被处罚人的司法救济权,不利于审理查明整个案件事实,亦可能导致整个违法建设的处理行为逃避行政诉讼的监督。
(四)对于行政机关制作的公文文书是否具有可诉性
应当探求行政机关的真意
从一般规则角度分析,认定函在性质上往往属于不同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行为,通常不直接对外产生法律效果,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范畴。但从特定情形角度分析,实践中不排除存在认定函实质外化,给当事人设定义务,从而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情形。因此,判断认定函是否可诉,根本上取决于对司法解释有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之规定的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不宜泛化认定相关实际影响而将认定函一律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亦不可片面限缩援引司法解释的规定而将认定函一律拒之门外。因此,要结合认定函内容的具体情况,看是否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产生重要影响和侵害,是否存在明确设定或者改变其权利义务的情形,是否确有必要对在此环节所作的行政行为的实体、程序合法性单独进行审查判断,从而对不同表现情形的认定函之可诉性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应当注意的是,如果规划部门所作认定函仅是客观告知(陈述)涉案建筑是否取得规划许可,从而认定其是否为违法建设,未设定或改变建筑物权利人的权利义务,则该认定函不具有可诉性。如果已经取得规划许可,规划部门在认定函中依据城乡规划法,明确认定涉案建筑属于尚可或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违法建筑物,此时,认定函实质上给当事人设定了义务,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则该回复具有可诉性。
综上,对行政行为可诉性的认定,关键在于审查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是否产生实际影响,不能仅仅从名称或者形式上判断。如果行政机关以“批复”“函”或者“会议纪要”的形式确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则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了实际影响,应当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否则,如果仅仅从公文名称上判断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可诉,就可能导致行政机关采取此类形式的行为而免于受到司法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