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加莎·克里斯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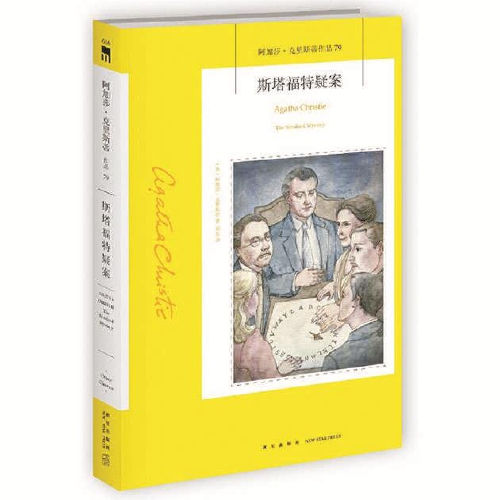
《斯塔福特疑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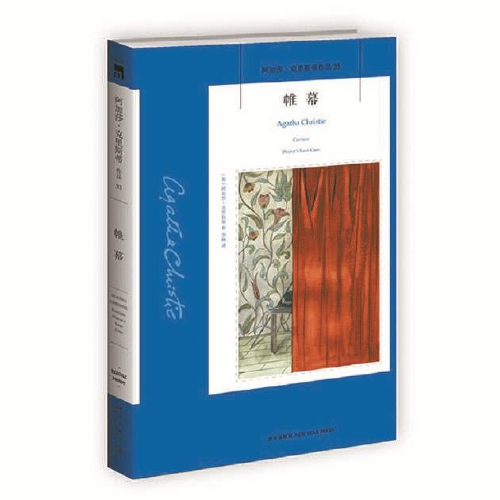
《帷幕》
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发表《莫格街凶杀案》,这是世界公认的第一篇侦探小说。之后,英国作家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宝石》、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等名作陆续与读者见面。及至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的作品问世,侦探推理小说步入黄金时代。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共创作80余部侦探推理小说,被翻译成100余种文字,西方文艺评论家称她是“侦探小说女王”,据说她的作品销售量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她的小说曾多次被搬上银幕,如《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等。
1.
阿加莎·克里斯蒂出生在英国,她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和幸福的童年。在她小时候,她的母亲经常给她讲故事和朗读文学名著,使她受到很好的文学熏陶。而她之所以能够走上创作道路,也离不开姐姐麦琪的影响。麦琪在家中是公认的才女,常在《名利场》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她经常绘声绘色地给阿加莎讲述福尔摩斯的故事。
16岁那年,阿加莎前往巴黎学习声乐,但因嗓音不好,最终没能当成演员。在母亲和姐姐的鼓励下,她开始创作诗歌和短篇小说,也经常与姐姐麦琪展开对侦探小说的讨论,这都对她后来的写作生涯大有裨益。阿加莎后来回忆说:“这些小说激发了我的热情,我向麦琪表示想写侦探小说。”麦琪没有支持妹妹,相反竟说:“我打赌你写不了。”阿加莎“发誓一定要写一部侦探小说,但没有立刻动笔,只是心里播下了这颗理想的种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加莎宁静的生活发生了变化。1914年,她嫁给了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一个皇家空军的飞行指挥官。当丈夫飞往法国执行任务后,阿加莎也毅然加入志愿服务队,被派往一家红十字医院。
她被分配在医院的药房工作。这里的工作不像护理那样忙碌,她开始考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写一部侦探小说。药房里都是药物、毒品,也许写投毒案的题材是最恰当的。阿加莎构思了小说的主要情节,最难的是故事中的人物,投毒者是谁?受害者是谁?他们又是什么关系?……
她在电车、火车、饭馆里,得到了对一些人物雏形的启发。一次,她在电车上碰见了“一位下颌蓄着黑胡子的男人,旁边的老妇人喜鹊似的叽叽喳喳没个完。那个女人倒不中意,男人却非常合适。旁边不远处还有一个胖女人高声谈论着卷心菜,相貌也很让人感兴趣”。阿加莎在写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有时设计好了开头,安排好了结尾,中间的部分却很不容易填满,往往书写到一半就陷入困境,因为那些错综复杂的情节搞得她不知所措,很难驾驭。
不过,阿加莎的创作得到母亲的支持,母亲建议她去休假,利用休息时间写完小说后半部。休假时,她订了一个房间,不与任何人来往。每天上午埋头疾书,下午散步,散步的时候就思考将要写的那一章,有时就会不知不觉地进入角色之中。假期结束时,她完成了最后几章,书名叫《斯塔福特疑案》。她把书稿寄给一家出版商,却很快被退了回来。之后,又寄给几家出版社,都得到同样的命运。又过了很多年,一家名为博得利·黑德的出版公司总算同意出版了。这本书的作者署名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共卖出2000册。从此,阿加莎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
2.
在《斯塔福特疑案》一书中,阿加莎塑造了大侦探赫克尔·波洛的形象。从此,波洛在她的25部长篇小说和许多短篇小说中不断出现,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
波洛这个人物是怎么产生的呢?在侦探推理小说中,当然需要有一名侦探,阿加莎考虑到,她的这位侦探一定不能与福尔摩斯相同,因为福尔摩斯是永远不能超越和模仿的,必须物色一个新人物。开始,她曾想塑造一个科学家,但她对科学家了解甚少。后来,她想到自己居住的地方有很多侨居的比利时难民,这些人的职业各式各样,一定也会有退休的警官。于是,阿加莎决定塑造一个比利时侦探:他当过检察官,懂得一些犯罪知识,而且应该是一个精明、利落的矮子。这样,一个足智多谋、思路明晰的比利时侦探就诞生了,最后阿加莎给他定名为赫克尔·波洛。
波洛这个人物在小说《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中大获成功。后来《随笔》杂志又约阿加莎写了12个有关波洛的故事,波洛从此名扬天下。同时,波洛与黑斯廷少校紧紧拴在一起,他们是理想的破案搭档,这也遵循了福尔摩斯系列的创作模式——性格古怪的侦探和形影不离的助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加莎担心自己能否活下来,就写好了以波洛为主角的侦探故事的结尾,也就是《帷幕》,小说写成之后就被锁进了保险柜。1975年,她决定再也不创作侦探小说了,才同意将《帷幕》出版。1975年8月6日的《纽约时报》破天荒地在头版刊登了波洛去世的讣告和新出版的这部小说的封面,这是该报第一次刊登虚构人物的逝世消息,可见波洛这个人物影响之大。
阿加莎有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可是她的这种观察力与她的毒药知识相比,就显得逊色多了。《斯塔福特疑案》出版后,《药学杂志》曾评论说:“这部侦探小说不同于那些胡编乱造的投毒案小说,它显示出作者丰富精深的药理知识。”正是这种丰富精深的药理知识,使她的作品更具魅力。阿加莎对下毒细节、中毒症状的描写十分准确,以至于有人说她的小说是“精确的医学教科书”。1961年出版的《白马酒店》一书中,阿加莎描写了凶手使用铊杀人的案例。14年后,一位南美妇女写信给阿加莎,说她根据《白马酒店》中对铊中毒症状的描写,发现并抢救了一位慢性铊中毒的男子。还曾经有一个病人已经死亡,正在准备火化,法医根据阿加莎小说中有关铊中毒的知识找到了凶手。
阿加莎还被誉为“香肠机器”,因为她可以在数周或数月内从容地完成一部小说,按期付印,作为圣诞礼物献给广大读者。在她的小说中,人们也不难发现她的为人及处世哲学。在《谋杀已被通报》一书中,她借玛普尔小姐之口说出的一番话正是她人生观的真实写照:“对世界怀有妒忌的人们是极其危险的。他们总认为生活欠了他们什么,这就是悲剧发生的根源。”
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加莎和丈夫、女儿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在此期间,她又完成了几部小说。
1926年12月3日,她突然失踪了,人们发现她的轿车被遗弃在伯克郡的路旁。各家报纸纷纷刊登这条消息,数百名警察、士兵和市民到乡下寻找她。12月14日,在一家旅馆里,两个乐师发现一位女性旅客与她十分相像,立刻报告了警察局,警方又通知了她的丈夫克里斯蒂上校。他赶到旅馆,证实了这个人就是阿加莎,但上校告诉记者:“她已经认不出我了,她完全丧失了记忆。”
有人猜想,这大概是女作家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力而耍的一种花招。因为在女作家失踪期间,她的小说被抢购一空。也有人推测,女作家是在构思一部新小说,她在体验生活。
可是,他们都错了。阿加莎不愿向外界谈及这次事件的真相,因为真相是那样残酷:她最亲爱的母亲去世了,同时克里斯蒂上校告诉妻子,他已经爱上另一个女人,并决定同妻子离婚。阿加莎一下子失去两位亲人,沉重的打击使她患上了记忆缺失症。因为患病,她不认识自己的家,不认识丈夫,忘记了自己过去的一切。
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阿加莎终于恢复了记忆。1928年,她和丈夫离婚并开始了中东旅行。1930年,阿加莎来到了伊拉克,在那里遇见了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不久后,他们结为伉俪。阿加莎陪伴丈夫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度过了许多年,她一面同丈夫研究考古学,一面从事写作。之后她发表的作品大部分仍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字,有时也用第二个丈夫的姓,署名阿加莎·马洛温。
阿加莎共写过17部剧作,其中《捕鼠器》(又名《蒙克斯威尔庄园谋杀案》)独占鳌头。该剧于1952年11月25日在伦敦使者剧院首演,被译成多种语言,在42个国家上演,创造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至今仍很受观众欢迎。
这个剧原先只不过是一个广播短剧。写作的起因是英国广播公司知道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表示喜欢阿加莎的作品,就约她为给女王安排的专题节目写一出剧目。为此,阿加莎构思了一个自己很满意的故事,名字叫《三只瞎老鼠》,后来又改编成三幕惊险剧,改名为《捕鼠器》。剧中有三个主要人物:一位年轻的姑娘,她诅咒生活,决意只为未来而活着;一个小伙子,他不愿面对生活而渴望母爱;还有一个小男孩,他幼稚地要对伤害人的残忍女子复仇。这个故事情节,是阿加莎根据现实生活中两个类似的案例构思而成的。
这样一个内容并不复杂的剧目,为什么会如此受到观众的喜爱呢?阿加莎在谈到成功的秘诀时说:“唯一的理由是适合大众的口味。不论年龄大小,兴趣如何,人人都喜欢看。故事层层展开,观众急于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事,却又猜不着下一步会怎样。尽管所有经久不衰的剧本都有这种趋势,但仿佛剧中人或迟或早总在装假,可《捕鼠器》的角色却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物。”
为表彰阿加莎在文学上的成就,英国女王于1971年授予她女爵士封号。1976年1月12日,阿加莎在英国去世,但全世界读者对她的作品的好奇心有增无减,她的小说不断地被搬上银幕和屏幕,美国公共电视台的“神秘”系列节目几乎成了她的天下,在我国,阿加莎也有非常多的忠实粉丝。









